近日,彼得·蒂尔(Peter Thiel)与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罗斯·道森(Ross Douthat)进行了对谈,内容涵盖科技停滞(Technological Stagnation)、人工智能、火星殖民、长寿、政治、宗教等主题。蒂尔在本次访谈中展现出罕见的多维思考能力。他将技术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政治有机交织,提出了诸多颠覆主流的观点:
- 技术停滞的根源不仅在科学瓶颈,更在制度与文化的抑制;
- AI虽是希望,但也可能成为平庸的加速器;
- 火星、长寿、永生已不再是乌托邦,而是政治逃逸的象征;
- 敌基督(Antichrist)可能是环保主义与技术监管的合体,而非传统意义的独裁者;
- 人类必须用自由意志抵抗平庸之神,用冒险精神打破停滞之网。
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精英的哲学反思,更是一份关于当代文明走向的“文化战略预警”。在AI、火星、长寿等看似宏伟的口号背后,存在着危机和风险: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未来,其实可能正在构筑一个完美的笼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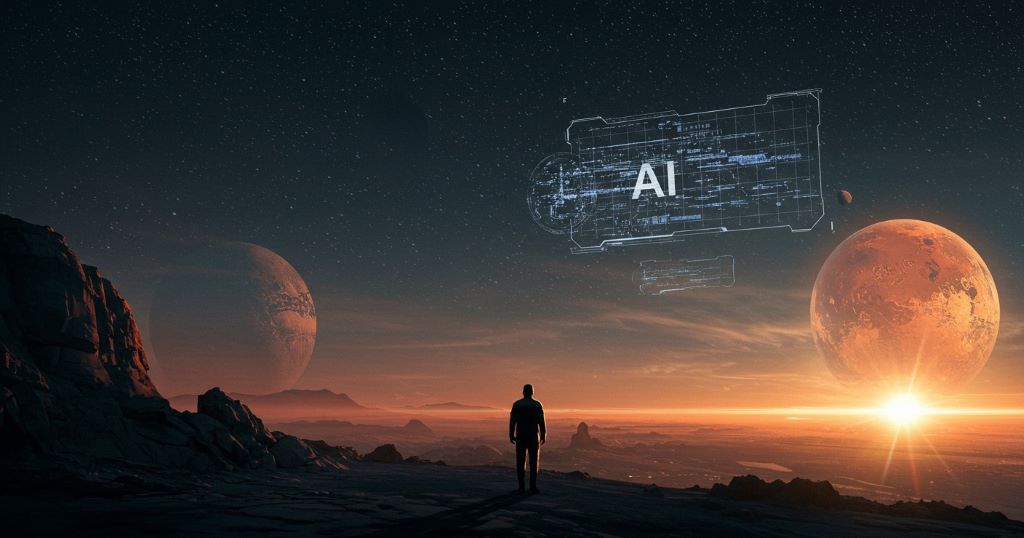
一、科技进步的假象与真实的停滞
彼得·蒂尔重申了他十多年前的核心观点:尽管数字科技(计算机、互联网、移动网络)取得了一定发展,但整体而言,我们正处于一个“科技停滞”的时代。他指出,从1750年到1970年,科技变革是加速的,如交通工具不断提速、能源形态持续跃迁,而这一趋势在1970年代后显著减弱。即便AI或区块链等技术在过去15年内崛起,仍不足以打破这一宏观停滞趋势。
他用《回到未来》电影作类比,指出1985年设想的2015年(飞行汽车等)远比实际到来的2015年更具颠覆性,这也反映出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落差。他强调,这种停滞不只是经济问题,而是一种文化和心理现象。
二、中产阶级的幻灭与社会秩序的失衡
蒂尔将“中产阶级”定义为“相信孩子未来会比自己更好的人群”。他指出,一旦这种信念瓦解,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失衡,甚至走向瓦解。他批评当前制度严重依赖经济增长(如消费资本主义、低税收社会主义等),一旦增长停止,政治与制度便难以维系。
他还认为,人类曾因对环境破坏、核战争等忧虑而主动接受科技减速。但他质问:“如果不走向未来,我们还能维持怎样的社会秩序?”他担忧,在风险规避成为文化共识的今天,社会最终会自我崩塌或陷入新的极权形式。
三、衰败中的幻想与冒险精神的缺失
蒂尔强调当代人普遍缺乏“做大事”的雄心。他批评现代医学在诸如阿尔茨海默症领域几十年毫无进展,但制度却无法推动重大突破。他主张大胆冒险,比如在反衰老研究中减少FDA限制、加快临床尝试。他怀念20世纪初那种“人类可以征服疾病、实现永生”的科学精神,而如今这一信念已随婴儿潮一代的老去逐渐消散。
他用冷峻的幽默回忆曾经为PayPal团队组织的“冷冻派对”(讨论人体冷冻技术),既展示了科技边缘幻想的荒诞性,也揭示了人类对死亡与永生的执着探索。
四、政治破局的幻想与现实的失望
蒂尔将自己对川普的政治支持比作一次“风险投资”,希望通过“干扰者”打破政治常规。他坦言,当初幻想川普当选后可以开启对“美国衰落”的坦诚对话,但现实远非如此。他认为,虽然川普并未带来实质性突破,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更多人承认“事情出了问题”。
他批评主流精英(如谷歌施密特、亚马逊贝索斯)在2010年代初集体沉浸于技术乐观主义,而如今硅谷已开始意识到停滞问题,部分科技大佬也转向支持保守主义甚至川普主义,虽非出于意识形态,而是因为“进步主义已无效,必须换药”。
五、AI:唯一的希望还是更深的幻象?
蒂尔对AI持一种“理性怀疑”的态度。他认为AI可能像1990年代的互联网那样带来一定经济增长(GDP每年增长1%左右),但尚不足以终结全面停滞。他担忧社会对AI寄予过高期望,如“超智能AI将自动解决癌症、制造自动化、建造火星基地”等幻想。他强调,许多问题的停滞根源不是智力缺失,而是制度与文化的压抑。
他提出一个极具洞见的批评:“如果AI变得聪明但高度保守与顺从(即woke),它也许只是加深停滞,像Netflix算法一样生成无限的‘尚可’内容。”AI可能使人类被动接受平庸,从而陷入“高智商的停滞”。
六、马斯克的“火星政治梦”与AI对乌托邦的侵蚀
蒂尔还批评了马斯克从“火星殖民”转向“预算赤字战争”的心态变化。他指出,火星曾代表一种政治愿景——逃离地球上腐朽的制度,建立新社会,但马斯克逐渐意识到“觉醒的AI与社会主义政府将追随人类到火星”,从而放弃了火星的政治理想。
他引述一次马斯克与DeepMind创始人的对话:“AI 会追随你到火星”,这一观点象征着乌托邦被技术阴影笼罩,科技已不再是解放工具,而可能成为极权延伸。
七、反乌托邦的终极隐喻:敌基督的崛起
在宗教维度,蒂尔抛出一个令人震惊但耐人寻味的论断:我们正走向一种以“和平与安全”为名义、打着“防止AI灾难”“避免全球变暖”等旗号建立的全球性温和极权,这种一统世界秩序可能就是《圣经》中“敌基督”的政治原型。
他警告,当人们不断谈论“终极风险”、“末日来临”,最终会促成一个“以技术监管名义接管全球”的制度,其本质是“阻止一切创新”的文明终结。而所谓“和平与安全”口号,正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中敌基督的口号。
他总结道:今天的“反科学者”不再是疯子科学家,而是“以阻止科学为政纲”的环保主义者、技术审慎主义者。他甚至调侃:“与其说你怕终结者,不如说你会甘心追随一个承诺让你永远不上网的新政权。”
八、自由意志、上帝与人类命运的博弈
在结尾,蒂尔以一种反宿命论的姿态收束了对敌基督与历史终局的讨论。他强调,基督教并非一切皆命定的加尔文主义,历史中仍有“人类自由行动”的空间。即便身处长久的停滞中,也不应选择麻木或屈服。他拒绝“上帝已经弃我们而去”的宿命思维,转而倡导主动应对、拒绝平庸的实践精神。
他援引耶稣被无故恨恶的经文(约翰福音15:25)为例,说明不能将一切责任归于上帝。他主张行动、警觉、承担责任,既警惕敌基督的技术极权,也拒绝在“屏幕与格蕾塔·通贝里”的画面中永久沉溺。